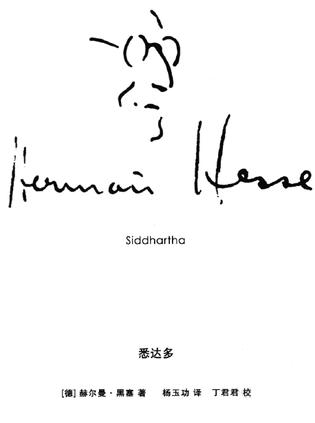作者: [德] 赫尔曼·黑塞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杨玉功 译 / 丁君君 校
出版年: 2009-3
页数: 157
定价: 20.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081628
p35
妓女在卖身,恋人在做爱,祭司在决定播种的季节,母亲们在抚慰她们的孩子——所有这一切都不值一看,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散发着谎言的恶臭,一切意义、快乐或美丽皆是幻象,一切皆是虚妄的腐朽。世界充满幸酸,生命即是苦痛。
悉达多只有一个惟一的目标——使‘自我’化为空无,抛却一切渴望、欲念、梦想、快乐与悲伤——让自我死灭;在空寂的心灵中寻得安宁。在抹除了自我的思维中等候奇迹——这就是他的目标。当自我被征服而寂灭,当心中所有的激情和欲望都归于静默,那终极之物必然会觉醒,那非自我的最深层存在,那伟大的秘密。
一只苍鹰飞越竹林,悉达多将那只苍鹰摄入自己的灵魂。他飞越森林和山峦,他化为一只苍鹰,猎食鱼类,忍受苍鹰的饥饿,使用苍鹰的语言,经历苍鹰之死。一只死去的豺躺在沙滩上,悉达多的灵魂溜进豺的尸体,化为一只死去的豺,躺在沙滩上肿胀,发臭,腐烂,为鬣狗所肢解,为兀鹰所啄食,化为残骸与尘土,最终融于大气之中。悉达多的灵魂死去,腐朽,归于尘土而重又复活,体验了生命轮回的阴郁魔 力。……他是动物,是尸体,是岩石,是木,是水,而每次他都再度清醒,在日光下,在月光中,他又成为自我,再次投入生命的轮回,再次感到渴望的躁动。征服了旧的渴望,又会感到新的渴望。
然而尽管所有这些修行使他远离自我,最终却仍旧引导他回到自我,尽管悉达多千万次地逃离自我,宅于虚无,宅于动物或岩石,但回归却总是无可避免。在无可挽回的回归时刻,他在阳光下,在月华里,在阴影中,或在雨中再度发现自己,再度成为自我和悉达多,再度感受生命循环的繁重折磨。
悉达多则轻声道,仿佛在自言自语:“什么是冥想?什么是对肉体的弃绝?什么是戒斋和调息?那只不过是在逃离自我,只不过是对自我所受苦难的一种短暂的逃避,只不过是针对生命荒谬与痛苦的一副暂时的麻醉剂。一个牧羊人在小酒馆里喝几碗米酒或是椰子奶时,他也在做同样的逃离,也在用同样的麻醉剂。于是他不在感觉到自我,不再感受到生命的苦难,于是他找到了暂时的逃避。那碗米酒使他昏然沉入睡乡,他同样找到了悉达多和侨文达在长时间修行中逃离肉体并宅于非我之境时所找到的感觉。侨文达啊,就是这样。”
p57
他深沉地冥想,直到完全沉入那种深潭般感觉的最底处,直到他认识到事物的因缘;因为在他看来,认识到事物的因缘就意味着思想,而只有通过思想,感觉才成为知识并且不会失去,而是变得真实,其内在熠熠生辉。
p58
另一种意念会立刻从前念之中浮现出来:“之所以我对自我一无所知,之所以悉达多对我来说一直如此陌生与未知,只因为一点,只由于这惟一的原因——我害怕自我,我在逃避自我。我在追寻梵天,阿特曼。我欲求摧毁自我、摆脱自我以便在自我未知的最深层发现万相的核心,即阿特曼、生命、神灵或绝对终极之物。而正因为如此,我却一路丢失了自我。”
p70
悉达多也感到全身涌起的一种渴望和性欲的骚动。但他以前从未碰过女人,他犹豫了一会儿,尽管他的手已随时要去攫住那女人。在这一瞬间他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而这声音说:“不!”于是所有的魔力都从那年轻女人的笑脸上立刻消失无踪,他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情欲亢奋的雌性的热切目光而已。他轻轻抚摸一下她的面颊,随后就离开这个失望的女人并很快消失在竹林之中。
p91
他经常拜访美丽的伽摩拉并向她求教情爱的艺术,而世上万法,尤其在情爱之中的付出与拥有才融为一体。他与伽摩拉交谈,向她求教,给她以劝告并接受她的劝告,她比以前的侨文达更能理解他,她更像他。
有一次他对伽摩拉道:“你很像我,你的确与众不同。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他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我也会这样做。极少人具备这种能力,然而所有人都能够获得。”
p102
自从他初次听见自心的声音,自从他高翔在思想的天空到现在竟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他的道路竟是如此无聊和荒凉!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崇高的目标,没有任何心灵的渴望,没有任何精神的升华。他竟一直汲汲于那些微不足道的享乐却从未有过真正的满足!在不知不觉之中,所有这些年一直渴望并努力生活得像这些尘俗人们一样,像这些孩童一样;而他的生活比世人的生活更加不幸和可怕,因为世人的目标不属于他,世人的悲伤也不属于他。这个伽摩湿瓦弥的整个世界对于他仅仅是一场游戏,仅仅是人们观看的一场歌舞、一场喜剧而已。惟一值得珍重和有价值的是伽摩拉;但是她是否仍值得珍重呢?他还需要她吗?或者说她还需要他吗?难道他们不也是在玩一场没有结局的游戏吗?还有必要继续为此而生活吗?不,这场游戏即是轮回,一场孩童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如果玩上一次、两次甚至十次还可以是有趣的,但接连不断地进行这种游戏是否还值得呢?
p118
现在他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自心之声是对的:没有任何导师能够给予他救赎。这就是为什么他必须进入尘世并沉湎于权力、女人和金钱;这就是为什么在他自心中的祭司与沙门死去之前他必须成为商人、赌徒、酒鬼和富人。因而他也必须经历那些可怕的岁月有,遭受恶心的折磨,彻底认清尘俗生活的空虚和疯狂,直到他陷入痛苦而绝望的境地;只有如此,他自心中的浪子悉达多与富人悉达多才能死去。事实上他已然死去,一个新生的悉达多已从他的睡梦中觉醒;这新生的悉达多也同样会衰老和死去。悉达多本为无常,一切形态皆为无常;然而今天他很年轻:他只是一个孩子——新生的悉达多——而且他也非常快乐。
p150
悉达多凝视着河水,流动的水面浮现出许多形象。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孤独地为失去爱子而哀痛;他也看到自己,孤独一人,无法摆脱对远方孩子的思念;他还看到自己的儿子,也是孤独一人,沿着燃烧的欲望之路急切前行。每个人都执著于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目标所困扰,每个人都在经受痛苦。河水之声忧伤,带着悲哀与渴望,向自己的的归宿流去。
p157
“不,我正在告诉你我的发现。知识可以传授,但智慧不能。人们可以寻见智慧,在生命中体现出智慧,以智慧自强,以智慧来创造奇迹,但人们不可能去传授智慧。我年少时就有过这种疑问,正是我的怀疑驱使我远离教师们。我还有过一种思想,侨文达,你又会认为那是玩笑或只是一种愚蠢的念头,就是说,每一真理的反面也同样的真实。比如说,只有片面的真理才能形诸于言辞;事实上,以语言表达或思维的一切都只能是片面的,只是半个真理而已,它们都缺乏完备、圆融与统一;当佛陀世尊宣讲关于世界的教义,他不得不把世界分为轮回与涅磐,虚幻与真如,痛苦与救赎。人别无选择,对于那些要传授教义的导师们来说尤其如此。而世界自身遍于我之内外,从不沦于片面。从未有一人或一事纯属轮回或者纯属涅磐,从未有一人完全是圣贤或是罪人。世界之所以表面如此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幻觉,即认为时间是某种真实之物。时间并无实体,侨文达,我曾反复悟到这一点。而如果时间并非真实,那么现世与永恒,痛苦与极乐,善与恶之间的所谓分界线也只是一种幻象。”
p158
“听着,我的朋友。我是罪人,你也是罪人,而罪人有朝一日会成为梵天,有朝一日会证得涅磐,有朝一日会成佛;然而这‘有朝一日’只是某种幻象,那只是一种比较而已,罪人并不是在趋于佛境,他并没有不断演进,尽管我们的感官只能如此感知事物。不,潜在的佛性已然存在于罪人身上,他的未来已然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隐藏于你、我以及所有人中潜在的佛性。侨文达,世界并非不完善,也不是正沿着通向完善的漫漫长路缓缓发展。不,世界在每一瞬间都是完美的:所有罪孽都已然领受神恩,所有孩童都是潜在的老人,所有的婴儿都已打上死亡的印记,而所有的垂死者必获永恒的生命。一个人不可能认清另一个人已然修到何等境界。佛存在于劫匪与赌徒身上,而劫匪亦存在于婆罗门身上。在极深禅定之中,人可以除灭时间并同时经历所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于是一切皆善,一切完美,一切即梵。因此,我认为一切的存在皆为至善——无论是死与生,无论罪孽与虔诚,无论智慧或是蠢行,一切皆是必然,一切只需我的欣然赞同,一切只需我的理解与爱心;因而万物于我皆为圆满,世上无物可侵害于我。我通过我的灵魂与肉体得知,我之堕落乃为必需,我必然经历贪欲,我必然去追逐财富,体验恶心,陷于绝望的深渊,并由此学会去抵御它们;学会热爱这个世界,不再以某种欲愿与臆想出来的世界、某种虚构的完善的幻象来与之比拟;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热爱它,以归属于它而心存欣喜。侨文达,这就是我头脑中的一些观念。”
p159
“看,”他手持石子道,“这是一枚石子,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它也许会化为泥土,泥土中会生出植物、动物或是人。我以前或许曾说过:这石子只是石子,毫无价值,属于玛耶女神的空幻世界,然而或许因为在变易之轮中它也有变为人或是神灵的可能。所以这枚石子才具有某种重要性。这或许是我曾经沉湎于时间之流而有过的想法,但是现在我认为:这石子不仅仅是石子,它同时也是动物、神或佛。我不因为它变换的可能性而尊敬它,爱它。而是因为它久远以来即包容了一切万物,而且永远涵摄万物。我爱它正是因为它是一枚石了,因为现在此刻它向我显现为一枚石子。我在它的每一细微的纹理和孔洞中都看到了价值与意义。它的灰与黄,它的硬度以及敲起来的声响,它表面的干与湿也同样显示着神秘与价值。有些石子摸起来像油脂或肥皂,有些看起来像树叶或沙子。每一枚石子都与众不同,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祷念着圆满的“唵”字真言。每一石子皆为梵。同时,不管是像油脂或肥皂,它又仅仅是石子而非其他。这正是使我喜悦之处,这正是奇妙而值得礼敬之处。——可我不想再谈下去,言辞不能很好地表达思想。思想一旦形诸言辞即刻就会有所改变,有所歪曲,有点愚蠢。对一个人显示着价值并充满智慧的词句对另一个人也许是一派胡言;然而即便是这一点也使我颇感欣喜,我也是认同的。”
p160
“你为什么给我讲那么多有关石头的事情呢?”他稍停片刻,犹疑问道。
“我并非有意这么做,但这或许说明了我爱石头、河流以及一切我们观看和师从的万物。侨文达,我可以去爱一枚石子、一棵树或一片树皮,这些都是‘物’。一个人可以去爱世上之物,但一个人不能去爱词句。所以教义于我毫无用处。那些教义没有软硬的感觉,没有颜色,没有尖角,没有气息和味道,它们只是一些词句而已,可能就是这一点阻碍你得到内心的宁静。也许世上词句过多,因为甚至连救赎、德行、轮回与涅磐都只是词句,侨文达。涅磐并非实在之物,世上只存在涅磐的名相。”